夏维波 教授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兼任中华医学会骨质疏松和骨矿盐疾病分会常委、候任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理事;卫生部合理用药专家委员会内分泌代谢组副组长;北京市糖尿病防治协会副理事长
 点击右上角"..."中的"
点击右上角"..."中的"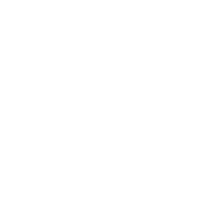 "按钮进行分享
"按钮进行分享

2019CEAAC|夏维波:中国人群40岁开始骨量降低,骨松防治关口要前移

打开微信”扫一扫“打开网页后点击屏幕右上角分享按钮
导语: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的生活水平日渐改善,医疗保健技术得到提升,随之而来的便是人口寿命的延长,老年人口数量便越来越多。但与老年人口如约而至的便是一些骨质疏松的患病。所谓骨质疏松,就是骨量低下、骨组织结构破坏、骨强度下降,继而骨小梁稀疏,容易发生断裂。其中,最易发生骨折的部位是椎体,其次是髋部、腕部或者是骨盆,严重影响了人民的生活质量。在本次年会中,夏维波教授带来了中国骨质疏松症的最新流调数据。
另外一个是髋骨骨折发生率的改变。在早期,全球髋骨骨折的发生率不高,但我们2012年做了一次研究,与1990年研究同样的方法,结果发现这十多年,北京地区的髋骨骨折发生率在增加,男性是129人/10万,女性是229人/10万,基于这个研究,澳大利亚与我们一起进行了一个预测,在这个预测中,2015年左右中国每年发生骨质疏松268万人,到2050年则有600万人,每年相关花费达1 600亿人民币。
那么中国到底有多少骨质疏松病人?之前一直未有一个合理的数据。基于这样的背景,我们与中国CDC及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一起进行了COPS中国骨质疏松患病率研究。



初级防治对象 是未发生过骨折但有骨质疏松症危险因素,或已有骨量减少(-2.5<T≤-1)者,应防止发展为骨质疏松症。目的是避免发生第一次骨折。
二级预防和治疗 已有骨质疏松症(T≤-2.5)或已发生过骨折。目的是避免初次骨折和再次骨折。
那么基于我们刚才说到的骨量变化规律,就是中国人40岁以上人群中骨量减低比例已相当高,骨量流失(尤其是松质骨)已较严重。这时候就要开始预防,要关口前移。这是我们提出的第一个策略。
早期筛查,推荐在40岁开始BMD的测定,以早发现骨量下降和骨质疏松的出现。关于这一点,我们希望能从40岁开始,将BMD检查纳入体检范围,这样就能早发现和早干预。当然,这个目前也在跟国家卫计委在起草计划中。另外一点就是要积极干预,以生活方式干预为主,确实诊断骨质疏松或者存在较多危险因素要开始药物干预,如HRT、SERMS等。
骨健康基本补充剂:钙剂和维生素D,但要注意,不推荐使用活性维生素D来纠正维生素D缺乏,也不建议1年单次较大剂量地补充普通维生素D。再有就是,针对已经出现骨质疏松或骨折的人,我们的重点是避免初次骨折或再次骨折。这个时候我们看我们的诊疗流程,特别是已经发生骨质疏松症或发生骨折的人,要开始治疗,而具有一些相关因素的,要建议生活方式干预,视情况进行基础治疗,这类人通常有这几种:骨质疏松者、骨量正常但有高危险因素者、脆性骨折者和骨量减少但合并危险因素者。
那么对于高骨折风险的筛查,又有哪些手段呢?传统的评估方法有以下几种:
1.根据各国人群特异的FRAX判断绝经后妇女的骨折风险,中度风险者采用BMD测定进一步判定;
2.若无BMD结果,直接使用FRAX判断;
3.小梁骨评分(TBS)作为BMD和FRAX的补充;
4.FRAX评分还需要考虑GC,LS-BMD,TBS,Hip-AL,跌倒史,2型DM等的影响;
5.椎体骨折评价一般要有几点:身高降低≥4cm,驼背,近期或长期使用GC,或BMD T-score≤-2.5。
对于高骨折风险的筛查及诊疗路径,不同国家也给出了不同的方法,而Russow等人在线发表的论文均指出,一次急性骨折后再发脆性骨折的风险显著增加,之后风险会逐渐降低;急性骨折后再骨折的风险极高,尽快给予预防性治疗可以避免更多的新骨折的发生;与抗吸收治疗相比,新近的促骨形成降低骨折的风险更快,作用更强;诊疗策略需要变化,尤其是针对极高骨折风险者。所以有骨折的病人要积极的治疗。那么对于高骨折风险患者的筛查就要关注既往骨折史,尤其是近期(<2年)骨折史,可能预示着更高的骨折风险,而对于骨折高风险的人群,应及时开始有效的药物治疗。
其中,药物干预有很多,基于骨折和髋部骨折的风险,分不同的药物干预阈值。

骨质疏松防治药物的选择
而对于骨折极高风险的治疗,要立即开始促进骨形成治疗,可能最大限度地降低骨折风险,一般来说,通常治疗18~24个月。而一旦停止治疗,效果立即衰减,其增加骨密度和降低骨折的作用需骨转换抑制剂维持。
代谢性骨病

夏维波 教授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兼任中华医学会骨质疏松和骨矿盐疾病分会常委、候任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理事;卫生部合理用药专家委员会内分泌代谢组副组长;北京市糖尿病防治协会副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