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右上角"..."中的"
点击右上角"..."中的"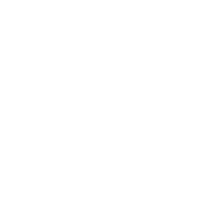 "按钮进行分享
"按钮进行分享

从饮食和健康的流行病学调查中总结到的方法论 ——临床学者需科学、严谨、冷静地看待研究结果

打开微信”扫一扫“打开网页后点击屏幕右上角分享按钮
导语: 随着第79届美国糖尿病协会科学会议(ADA 2019)的召开,各大研究结果争相发布。其中,关于饮食和健康的D2d研究和吃饭次序与时间研究备受关注,同时也饱受争议。代谢网小编整理了一篇2018年发表于Cell Metabolism上的综述,辩证、冷静地分析了2017年引起万众瞩目的PURE研究,总结了饮食流行病学的不同之处,指出随机临床试验在饮食流行病方面的局限性,和前瞻性队列研究的特点。希望这篇文章能给大家带来启示,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对待这些研究。同时,也希望本文能给大家的科研设计带来一些思考。
在许多确定的心血管疾病(CVD)危险因素中,饮食起着重要作用[1]。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许多研究增强了我们对饮食与心血管健康之间关系的理解。然而,不同研究带来的不同结果造成了患者、医务人员和一般公众的混淆。2017年的一项前瞻性城乡流行病学(PURE)队列研究在媒体上引起了轰动性效果以及科学界的争论。PURE研究旨在阐明常量营养素摄入量与死亡率之间的关系,但研究结果似乎与先前的研究和现行饮食建议和指南相矛盾。通过分析来自18个国家超过135 000人随访7年的自我报告的饮食数据,结论是高碳水化合物摄入量与总死亡率风险较高有关,而较高的脂肪摄入量与较低的总死亡率相关[2]。
要想辩证、客观、冷静地分析此结果,我们需要了解以下几点。
流行病学研究设计的最新进展
1. 随机临床试验的局限性随机临床试验(RCT)特别是那些高质量和双盲的试验,是确定各暴露因素和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黄金标准,更是医疗指南和卫生政策的基石(图1)。理想情况下,RCT应用于检查营养素或食物对心血管事件的影响,其方式与批准新药和医疗器械所需的方式相同。

图1 基于推断因果关系能力的典型研究设计层次
然而,RCT对许多营养素和食物(包括常量营养素)的研究有局限性:为了获得有效结果,治疗组和对照组之间摄入水平的差异必须具有生物学意义并持续足够长的时间,如对于心血管事件,干预期至少需要几年;另外,需要大样本量来获得足够的统计功效;其次,当将参与者分配到与其通常饮食不同的饮食时,也难以保持高依从率。
典型的是妇女健康倡议(WHI)随机对照膳食改变试验[3],研究目的是评估降低总膳食脂肪对癌症和CVD结果的影响。该研究在1993年-1998年期间招募了48 835名年龄在50-79岁之间的女性,并随机分配低脂肪饮食(20%的脂肪能量摄入量)或维持其通常的高脂肪饮食(37%的能量来自脂肪)。在平均8.1年的随访期后,低脂组的大多数人没有达到将脂肪减少到20%能量摄入的目标。试验结果显然未观察到低脂饮食对癌症或CVD结果的显著影响。
RCT研究中饮食干预的另一个挑战是参与者不能因饮食分配而实现双盲。在WHI试验中,干预组除了减少脂肪摄入量外,报告显示还有纤维、蔬菜、水果、全谷物和大豆摄入量增加。因此,难以分离特定常量营养素的作用。
尽管存在这些挑战,但如果控制良好的RCT研究对于检查营养素、食物和饮食模式对健康结果的影响以及制定基于证据的建议至关重要,如抑制高血压的饮食方法(DASH)和地中海饮食(PREDIMED)试验为支持健康饮食模式在高血压一级预防中的作用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4, 5]。
2. 前瞻性队列研究是饮食流调的首选
由于RCT的限制,前瞻性队列研究是检查饮食与CVD之间关系的首选观察性研究设计[6](图1)。通过这种设计,研究人员在一段时间内跟踪大量参与者,并且不干预改变饮食习惯。在许多队列研究中,当参与者入选时,在基线时收集膳食摄入量数据,并且在随访期间评估CVD和其他健康结果。膳食数据通常根据验证食物频率问卷调查(FFQ)或24小时膳食回忆计算,有时从多日膳食记录中收集。FFQ通常具有较少的随机错误,但由于遗漏食品和不准确的营养成分数据库而导致系统性错误,常见的解决方案是在分析中使用能量调节的营养素。由于特定营养素和总能量均来自FFQ中的相同食物,因此营养素和总能量的测量误差(过度报告或报告不足)可能相关[7]。统计上,可以通过调整总能量摄入来减少相关误差。此外,使用验证数据的重复饮食措施也减少了测量误差和错误分类的影响。
许多前瞻性队列研究已在美国和欧洲进行,例如Framingham心脏研究[10]、护士健康研究[11]和英国生物银行研究[12]。目前在发展中国家和正在经历快速营养和经济转型的国家也在进行队列研究,如中国嘉道理生物银行研究(CKB)[13],该研究从2004年开始在中国10个地区招募了512 891名成年人,该研究旨在调查中国人群中慢性病的生活方式、环境和遗传决定因素。
3. RCT和前瞻性队列研究结果不一致的原因
前瞻性队列研究和随机对照试验的结果可能并不总是一致的。例如,许多队列研究报道抗氧化维生素(如维生素C和E)与CVD发生率呈负相关[8],但大多数随机对照试验表明,补充这些维生素不会产生有益效果[9]。这种差异可能是由于RCT通常选择高风险人群,并且与观察性研究相比,补充的持续时间相对较短(3 - 5年)。此外,在观察性研究中,社会经济状况、更健康的饮食和生活方式可能部分解释了维生素与CVD风险之间的负相关关系。高剂量补充剂中的抗氧化剂可能与膳食来源中的抗氧化剂有不同的效果,膳食来源中的抗氧化剂与其他有益的营养素(如纤维、矿物质和多酚)混合在一起。
营养流行病学的另一个进步是能够在队列研究中测量储存的生物标本(血液、尿液或其他生物流体)的膳食生物标志物,并分析它们与疾病结果的关系。这可能是估算食物成分表中没有的营养素或者由于生产、储存、加工或制备过程中发生变化营养素摄入量的唯一选择。生物标记物是针对某些营养素建立的,例如,尿液中的蛋白质的量、尿钠/钾摄取的盐量等。需要注意的是,饮食生物标志物测量是营养流行病学研究中自我报告方法的补充,而不是替代[6]。
PURE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
从2003年开始,PURE研究在18个国家的135 000名参与者中使用FFQs收集自我报告的饮食数据[2]。花费7年时间观察参与者的健康状况,发现饮食中脂肪摄入量高的人死亡率比摄入量低的人少23%;相反,对于碳水化合物,那些摄入量高的人死亡率比摄入量最低人高28%。因此,作者得出结论,较高的脂肪摄入量与死亡率降低有关,而较高的碳水化合物摄入量与死亡率增加有关。虽然这项研究的样本量很大,包含许多国家的参与者,但由于以下方法问题,对于此结果仍需要谨慎解释。1、将所有碳水化合物放在一起过于简单化,因为不同类型的碳水化合物对健康具有相反的影响。研究一致表明,精制碳水化合物与风险增加有关,而全谷物与CVD和2型糖尿病风险降低有关[14, 15, 16]。
2、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人们还只属于“贫困饮食”,其中含有少量脂肪和许多精制碳水化合物,例如白米和精制小麦产品。因此,当试图比较高饱和脂肪摄入量和低饱和脂肪摄入量时,研究实际上将高饱和脂肪摄入量的参与者与高精制碳水化合物摄入量的参与者进行了比较。因此研究结果显示饱和脂肪与CVD没有显著关联,这并不奇怪,因为在分析中,饱和脂肪本质上是与精制碳水化合物相比较的。此外,碳水化合物摄入量与死亡率风险之间的关系主要是由非CVD死亡率引起的,例如呼吸道疾病、肝脏疾病和传染病死亡,而发展中国家低收入人群往往都承担这些疾病的负担,并且消费高碳水化合物饮食。因此,高碳水化合物摄入量与非CVD死亡率之间的关联可能会因贫困、粮食不安全、营养不良和缺乏医疗服务而受到混淆。
3、PURE研究人群高度异质,由来自18个国家的农村和城市地区的参与者组成,他们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且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饮食模式、食物选择、生活习惯和文化背景差异很大。因此,需要针对具体国家、特定区域以及城乡分层分析才能更好地理解队列研究中所观察到的关联。
4、PURE研究中提出的常量营养素组合物为50%碳水化合物,30%-35%脂肪,15%-20%蛋白质,非常接近目前的饮食建议[17]。因此,PURE研究结论提到的“根据这些发现应该重新考虑全球饮食指南”,这条并不受其自身数据支持。
5、构成PURE研究样本三分之一的中国参与者的膳食摄入量数据与中国其他研究的数据不一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脂肪摄入量一直在增加,碳水化合物摄入量减少,与这些饮食变化平行的肥胖、高血压和糖尿病的发病率显着增加(图2)。全国调查报告称,目前中国人口平均每天消耗30%的脂肪。然而,PURE研究报告中中国参与者的平均总脂肪摄入量为17.7%。PURE研究使用的FFQ与2002年中国国家营养与健康调查相同。PURE研究中膳食数据的巨大差异使人们怀疑PURE研究的膳食评估程序的有效性。令人惊讶的是,植物油是中国成年人膳食脂肪的主要来源,但并未列入PURE研究的膳食脂肪最佳食物贡献者名单。

图2 1992-2012年中国碳水化合物和脂肪摄入的能量趋势以及肥胖相关慢性疾病的增长
总之,尽管PURE研究数据来自多个国家的众多人群,但结果仍需要在现有文献和数据的背景下进行方法学分析和解释。总的来说,研究结果似乎没有对现有的饮食建议提出挑战。
在观察研究中推断因果关系的机遇和挑战
虽然不能在观察性研究中完全消除混淆和偏见,但仍可以基于证据的总体推断因果关系。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现在被广泛用于总结相关文献,综合数据。然而,如果对设计和执行不佳的饮食和健康研究进行荟萃分析就可能产生误导性的结果,并向公众传播不准确的信息[18]。在进行和解释关于饮食和健康的荟萃分析时,谨慎行事至关重要,因为荟萃分析容易受到限制。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饮食和疾病结果的随机对照试验都具有挑战性,但在可行的情况下仍应予以考虑。实验研究有助于深入了解将饮食与健康联系起来的潜在机制和途径,这是确定因果关系的重要因素。来自不同类型的研究设计的一致证据对于达成共识和推断因果关系是必要的。
参考文献
1. Forouzanfar MH, et al. Risk Factors Collaborators Glob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comparative risk assessment of 79 behavioural, environmental and occupational, and metabolic risks or clusters of risks in 188 countries, 1990–2013: a systematic analysis for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13. Lancet. 2015; 386: 2287-2323.
2. Dehghan M, et al. Rosengren Prospective Urban Rural Epidemiology (PURE) study investigators Associations of fats and carbohydrate intake with cardiovascular disease and mortality in 18 countries from five continents (PURE): a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Lancet. 2017; 390: 2050-2062.
3. Howard BV, et al. Low-fat dietary pattern and risk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 Women’s Health Initiative Randomized Controlled Dietary Modification Trial. JAMA. 2006; 295: 655-666.
4. Sacks FM, et al. Simons-MortonDASH-Sodium Collaborative Research GroupEffects on blood pressure of reduced dietary sodium and the Dietary Approaches to Stop Hypertension (DASH) diet. N. Engl. J. Med. 2001; 344: 3-10.
5. Estruch R, et al. PREDIMED Study InvestigatorsPrimary prevention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 with a Mediterranean diet. N. Engl. J. Med. 2013; 368: 1279-1290.
6. Satija A, et al. Understanding nutritional epidemiology and its role in policy. Adv. Nutr. 2015; 6: 5-18.
7. Willett WC, et al. Nutritional Epidemiolog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13.
8. Knekt P, et al. Antioxidant vitamins and coronary heart disease risk: a pooled analysis of 9 cohorts. Am. J. Clin. Nutr. 2004; 80: 1508-1520.
9. Myung SK, et al. Meta-Analysis Study Group Efficacy of vitamin and antioxidant supplements in prevention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s. BMJ. 2013; 346: f10.
10. Mahmood SS, et al. The Framingham Heart Study and the epidemiology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Lancet. 2014; 383: 999-1008.
11. Bao Y, et al. Origin, methods, and evolution of the three Nurses’ Health Studies. Am. J. Public Health. 2016; 106: 1573-1581.
12. Collins R, et al. What makes UK Biobank special? Lancet. 2012; 379: 1173-1174.
13. Chen Z, et al. China Kadoorie Biobank (CKB) collaborative groupChina Kadoorie Biobank of 0.5 million people: survey methods, baseline characteristics and long-term follow-up. Int. J. Epidemiol. 2011; 40: 1652-1666.
14. Zong G, et al. Whole grain intake and mortality from all causes, cardiovascular disease, and cancer: a meta-analysis of prospective cohort studies. Circulation. 2016; 133: 2370-2380.
15. Aune D, et al. Whole grain and refined grain consumption and the risk of type 2 diabete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dose-response meta-analysis of cohort studies. Eur. J. Epidemiol. 2013; 28: 845-858.
16. Hu EA, et al. White rice consumption and risk of type 2 diabetes: meta-analysis and systematic review. BMJ. 2012; 344: e1454.
17.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2010). Fats and fatty acids in human nutrition: report of an expert consultation. FAO Food and Nutrition Paper 91. http://www.who.int/nutrition/publications/nutrientrequirements/fatsandfattyacids_humannutrition/en/.
18. Barnard ND, The misuse of meta-analysis in nutrition research. JAMA. 2017; 318: 1435-1436.
其他












